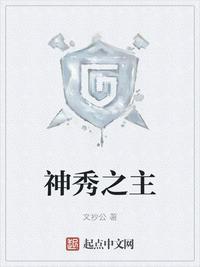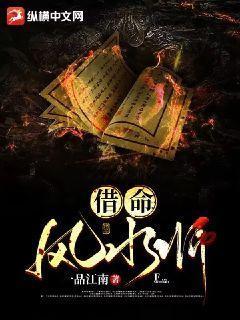耗子小说网>坐看仙倾 > 第407章 太古夜色终临二合一(第3页)
第407章 太古夜色终临二合一(第3页)
哭声、怒吼、哽咽交织成一片。苏晚悄悄展开护心网丝线,将其编织成环,笼罩整个教室。阿禾继续吹笛,这一次,他加入了新的旋律??不是安慰,不是劝导,而是纯粹的“我在”。
两个小时后,当他们离开时,黑板上的涂鸦已被擦去,取而代之的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字:
**“如果还有人愿意听,我们就还不算坏。”**
类似场景在全国各地上演。精神病院里,长期缄默的患者在笛声中开口讲述童年创伤;贫民窟中,毒瘾者主动交出针管,请求加入志愿者队伍;甚至某次集会上,激进组织首领听完直播演奏后,当众撕毁煽动宣言,哽咽道:“我女儿要是还在,也会喜欢这支曲子吧……”
共情的涟漪不断扩大,悄然改变着世界的质地。
春末,教育部宣布将“鸣心教育”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,内容包括情绪识别、倾听训练、非暴力沟通与集体疗愈实践。首批试点学校中,江南第七中学排名第一。
毕业典礼那天,阿禾作为学生代表发言。他没有讲稿,只带来一支全新的柳笛??由九种木材拼接而成,象征多元共生。
“这一年,我学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:**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行动。**”他说,“我们总以为改变世界需要惊天动地,可真正的转变,往往始于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,对另一个人说:‘我听见了。’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许多老师红了眼眶。校长悄悄抹泪,想起自己也曾因职称失败想过轻生,是某个学生递来的一封手写信让他撑了过来。
仪式结束后,陆鸣远将他唤至鸣心堂遗址。湖面平静如镜,守护灵的身影早已消失,唯余那盏琉璃灯静静漂浮,映照满天星斗。
“你要走了吗?”阿禾问。
陆鸣远微笑点头:“使命已完成。接下来的路,该由你们自己走了。”
“那你去哪儿?”
“回到风里。”他轻声道,“回到每一次善意升起的瞬间。当你帮助他人时,那就是我在看你;当你选择相信时,那就是我在陪你。”
说罢,他身形渐渐淡去,最终化作一缕青烟,随风散入群山。
阿禾独自伫立良久,忽然感到胸口一热。他掏出琉璃片,只见上面浮现出新的字迹:
**“传承者。”**
他笑了,将柳笛举向星空,吹响第一缕夏风。
远处,苏晚站在山坡上,手中丝线迎风飘扬。陈知寒在海岛点燃一盏河灯,送它漂向深海。百余名鸣心青年分散各地,或抚琴、或诵诗、或默默陪伴孤老。
而在宇宙尽头,九星再次排列,勾勒出三个新字:
**“正发生。”**
风仍在吹,带着笛声、笑声、低语声,穿过时间的缝隙,落入未来无数个清晨。
有人摔倒,立刻有手伸来;
有人哭泣,总会有人递上纸巾;
有人迷路,便会有灯光亮起。
这个世界依然不完美。
仍有战争、疾病、背叛与遗忘。
但每当黑夜降临,总有人记得??
只要还肯点亮一点点光,
春天,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