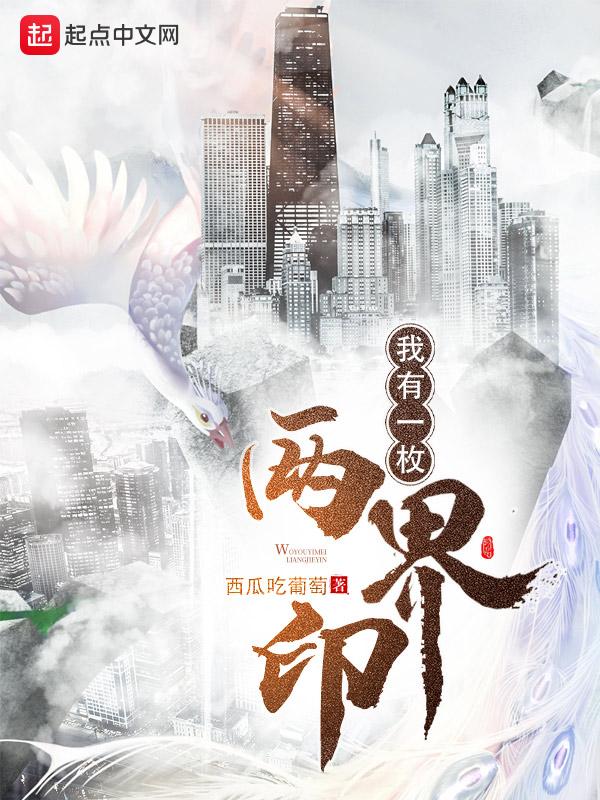耗子小说网>从小道士肝到玄门真君 > 第17章 确立天庭小山苏醒(第3页)
第17章 确立天庭小山苏醒(第3页)
他转头望去,只见一名小女孩牵着父亲的手走过雪地,头上风筝挂着小铃铛,绘着九阙图案。她一边跑一边喊:“爸爸!今天我们学了怎么问问题!老师说,不懂就要大声说出来!”
启明子怔在原地。
那一刻,他脑海中闪过童年记忆:他曾是个孤儿,在官府学堂读书,因提出“为何穷人不能考科举”而被打板子。后来他苦修二十年,终于悟出一套完美理论,认为只要统一思想、消除分歧,人间便可永享太平。
可现在,一个小女孩的笑声,竟让他毕生构建的逻辑大厦出现裂缝。
他低头看向掌心,那枚紫金烙印正缓缓褪色。
与此同时,苏婉儿登上孤岛最高崖,再次举起油灯。
她不再说话,只是将灯高悬于竹竿顶端,面向北方。
刹那间,全国各地的“问心墙”同时亮起微光,千万条手写的问题飘向夜空,如萤火汇流,形成一条璀璨银河,直指青铜巨门。
启明子仰头望着那漫天疑问之光,忽然笑了。
他撕碎手中经卷,轻声道:“原来……真正的道,不在答案里,而在问的路上。”
言毕,身影淡去,如雾消散。
青铜巨门轰然关闭,沉入地底,再无踪迹。
多年后,有人在那片焦土上种下了第一株白梅。几年后,花开满园,香气十里可闻。当地人称其为“问梅林”,每逢春日,学子们齐聚树下,不诵经,不讲义,只做一件事??轮流站在石台上,说出自己最近的一个问题。
没人规定必须解决,也没人嘲笑幼稚。
因为他们终于明白,王平当年点燃的,不只是希望,而是一种权利:
**每个人,都有权不明白。**
而苏婉儿依旧住在孤岛茅屋,年岁渐长,两鬓染霜。她不再频繁出行,却每日坚持写一篇短札,记录所见所感,寄往各地学堂。孩子们最爱读她的“灯下絮语”,其中有一篇写道:
>“小时候我以为,长大就是要找到所有答案。
>后来我才懂,成长是学会带着问题活下去。
>就像这盏灯,它的使命不是照亮整个黑夜,
>而是告诉每一个摸索前行的人:
>你看,还有人在走。”
某年冬至,她病卧榻上,气息微弱。弟子们围在一旁,含泪询问遗训。
她勉强一笑,指向窗台那盏油灯:“别担心熄灭。
真正重要的,从来不是哪一盏灯,
而是……
谁愿意,在黑暗里,再点一次。”
话音落下,窗外忽降瑞雪。
第二日清晨,人们发现,整座孤岛的“明心亭”不知何时全部点亮,火焰稳定,方向一致,仿佛被无形之手牵引。
而在最高的礁石上,插着一根蜡烛,火苗虽小,却倔强燃烧,照见海面倒影中,隐约浮现一行由浪花组成的字迹:
**“我在。”**
就像当年雪中那一盏灯,从未真正离去。